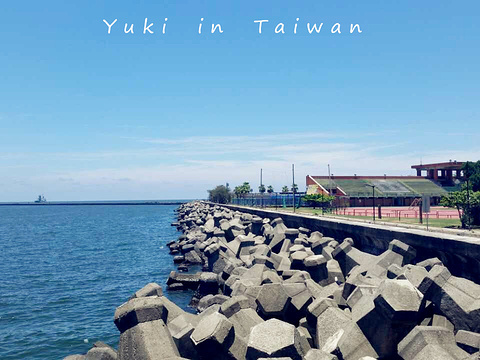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尼克•维尔维特是个贼。虽然他年轻时也曾投笔从戎(朝鲜战争),保家卫国,表现了高尚情操。然而,最终却在闯空门这行里打下一片江山。大好前程,如水东流。 不过,只要"钱"程似锦,一切OK。虽然尼克只偷不值钱的东西,然而雇他顺走这些东东滴主顾却都愿意至少掏出两万美刀。饶是如此,尼克的生意依然络绎不绝,可见他确实有两把刷子。 需要说明的是,小偷的圈子其实很小,一向厉行低调的伯尼•罗登巴尔也不得不面对自己贼名远扬的事实,就是明证。仰赖圈内人的口口相传,尼克只要安坐家中,自然会有委托找上门来。当然,找他的往往都不是什么居心正大的良善之辈。毕竟,好人没事会去雇贼?根据骨牌效应,一件罪行必将引出另一桩罪行。在那些奇特委托背后潜藏着多少罪恶,多少阴谋?不过这些都与尼克无关,他是有职业操守的贼,雇主的秘密他没有兴趣,除了完成任务和收取足额报酬,其他都不关心。然而,也许是曾经盗窃过行业守护神墨丘利塑像的原因,尼克失去了这位小偷之神的庇护。虽不至于像RPWT伯尼•罗登巴尔那样每次都遇上三五具尸体,但也经常遇上麻烦,甚至不能像伯尼那样守住一个小偷的非暴力节操底限!已经没有节操滴尼克,自然也不会顾及主顾需要保守点小秘密滴心情了。 所以,如果朋友您正巧身边有个两三万美刀,没地儿花,可别想去打尼克•维尔维特滴鬼脑筋。否则,任你再怎么高唱小龙人之歌,都没有任何用处的说。 虽然,尼克经常性滴没有节操,但他确实是当得起"卿本佳人"四个字。本书收录的十一个故事,都是尼克六十年代的做为。彼时的他,尚且未到不惑之年,莽撞有余,情义不足。然而,正如P228所言,"在尼克心里住着一个骑士,不断地搏杀着现代社会的恶龙,如果他追逐的圣杯只不过是金钱,又与凡夫俗子有何差别?"尼克本性中的骑士精神正在慢慢发展,终将凌驾于一切节操之上。尼克并非在行侠仗义,但他心中自有底线。他不忍弃身处险境的无辜女孩于不顾,也不会对杀人越货的强盗放任自流。尼克并不将所有罪犯都交给警察,毕竟大家都是法外之身,只要能阻止那不可饶恕的罪行ーー谋杀,都应该给别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毕竟,惩前毖后,也是以治病救人为主旨滴嘛。 难道这样的尼克•维尔维特不是一个贼佳人么?(这名词。。。好诡异。。。) PS:你可能会问,既然尼克心中有一个骑士,为何又会误入歧途,"奈何做贼"?难道不能弃恶从善,当个建筑工人啥的,和格洛丽亚一块儿喝着啤酒,消磨余生呢? 这个嘛,自然和其他屡教不改滴偷儿(比如今天乱入N次滴伯尼•罗登巴尔)一样,因为尼克是个小偷,他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变。

闲笔未让丹青妙
初晓得叶浅予,是小时在《连环画报》上看了节选的《王先生与小陈》。 立即就迷了进去,王先生和小陈招女秘书,来的却是自家老婆和女儿,哈哈!王先生谎说要去当官,骗小陈饯了一次又一次行,哈哈!小陈真上南京当官,火车不买票,却阔亲戚把查票员吓得噤如寒蝉,哈哈哈!王先生到山东去,看当地人憨厚,每次餐后会钞说钱包掉了,下次给,最后被一堆饭庄老板追打:“俺们山东有这么多贼吗?”哈哈哈哈哈哈…… 没看过原漫画的人一定觉得一点都不好笑。看过的呢,一定会觉得我的笔太笨,多好玩的漫画,被你写成这样! 这是真的,漫画有它独特的味道,别的方法替代不来,莫说在下一支拙笔,“王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走红后,十年内连拍了11部王先生影片,部部卖座,90年代张建亚导演《王先生之欲火焚身》,极尽反讽戏仿之能事,可是,尽皆过火,尽皆癫狂,怎样都传递不出叶浅予画笔下那种平易的、温润的、略带辛酸与悲悯的笑谑与快乐。 对于这位曾带给我的童年无穷欢乐的画家,我一直存着一份默默的感激。但是,《细叙沧桑记流年——叶浅予自传》不只是让你重温儿时的喜乐,它还掀开幕布,给你看看那个有一支魔笔的人,走过了一条怎样的道路: 上学,辍学,谋食,结婚,成名,分居,同居,分手,再婚,沦陷,逃难,访印,访美,教书,离婚,再再婚,被打倒,蹲大狱,丧子,丧偶。如许惊心动魄旧事,赢得细叙流年的云淡风轻。 我是极爱看自传的人——胡适曾大力提倡每个人都写自传,因为每个人都是一部活的历史。而自传中尤好看者,有两类:一是有心的传主,数十年日记不辍,而且大事小事有闻必录,他的日记不像方鸿渐尊翁的那样为了训示后人,也不像莎菲女士冰莹女士那般专记内心波澜,他似乎只是为了记录历史的断片,让后来人知晓,从前有过这样的日子,这样的人生。 另一类是有本事画出所见风物者。近两年出版的妹尾河童作品,是我见过此类人物的极品,见到每一样新奇的物事,每一处初到的所在,他都细细地量、描、画,他简直把自己的眼睛借给了你。 这两类自传的优点,在《叶浅予自传》中强强联手,水乳交融,一部四百余页的大书,记事、写人、绘景、传神,那才叫山阴道上,目不暇接! 优点不止这些,叶浅予的文笔出奇的好。不是胡兰成的浓稠绵密,不是张中行的絮絮叨叨,只是气定神闲,娓娓而谈。叶浅予记人生,文如其画,是“速写加线描”,几大部分轮廓分明,记游便记游,评画便评画,说受难,谈婚姻,都是寥寥几笔,其形立见,再细细描摹,引日记,引书信,一言一动,如在眼前。观念呢,在不新不旧之间,文字呢,不带欧化气息,文白互见,总之,一切皆有法度,不衫不履,却全无粗服乱头的小家子气。 读书时就发现,理科生的字大都比文科生强,因为理科生记笔记少,也不用笔混饭求上进;后来又发现,文艺圈中,美术音乐电影诸方家的文字,往往别成一格,不带匠气。不计功利,才能随心所欲,正如读书,读尽天下书,不过是书橱一只,把天下书都读成闲书,方是真读书者。 《叶浅予自传》真是一本闲书,是一本可以存留在架上,时时翻看的闲书。 至此本当收束,文人积习,口占得一绝,写下来。编辑先生嫌烦,尽可删去: 无人不识王先生,访印游美万里尘。 闲笔未让丹青妙,始信文章老更成。
这一生只留下刹那芳华只为你开
藤泽周平一定是一个很懂得欣赏女性的人。在这本书里面的女性,尽管着笔寥寥,但是无不透露着可爱和柔美。能温柔忍耐操持家务的妻子,明艳活泼喜欢开玩笑的初恋大姐姐。就连不那么孝顺的儿媳都做得一手好菜;连委身下嫁,抱怨不断的大小姐,都是个打扫卫生的能手。 清兵卫们可以忍受被叫做生瓜,马屁精,闷葫芦,邋遢鬼,可以忍受柴米油盐的琐碎,可以甘愿在日复一日的无聊工作中渐渐变老。但只要这些可爱的女性受到侮辱侵犯,即使素不相识,即使对方是达官贵人,不起眼的庸庸碌碌的清兵卫们,刹那间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和大丈夫。好像他们将平时所有的光彩和勇气都储存起来,只为在这一刻绽放。 二战时,苏联的伊万们爱唱《喀秋莎》,而德国的汉斯们爱唱的《Erika》。都是以年轻姑娘为主角的歌。许是家乡的姑娘比较能激起前方年轻人的勇气。然而勇气的来源不只是荷尔蒙。大多数小伙子在家乡并没有一个喀秋莎等他,而Erika更是一个开遍原野的小花的名字。《喀秋莎》和《Erika》唱的不只是爱情,唱的更是家乡,唱的是凡人习以为常的平淡生活。 男女风月,总会变成过眼云烟;夕阳炊烟,柳叶屋瓦,才是人间有情。对异性的爱,总是不如对家乡和生活的爱来得深沉浓郁。家老,中老等上位者们为了藩中权利,勾心斗角,阴谋迭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下位的平凡人上班领薪水,回家洗衣,做饭,照顾老婆孩子,只为平平安安,把日子过下去,能看到心爱的人的笑脸。美好温柔的女性们,是美好温柔的日常平凡生活的缩影,也是清兵卫们不可侵犯的最后底线。 大多数时候,我们靠自己的沉默,猥琐,懦弱和卑微铸成的保护壳苟活着,但是总有无法再逃避退让的时候,因为身后就是我们的温柔姑娘,我们可爱的家乡,我们所珍视的平凡生活,我们赖以支撑自己的信仰。我们已无路可退。 竹林桑说过,吾辈只是微尘,但是微尘也有自己要拼命守护的东西;也许吾辈只是微不住道的小虫,但是就算是小小萤火虫,有时候也想燃烧生命放出一点点米粒般的光亮;无权无势的吾辈的确只是一介匹夫,但是匹夫之怒也能让人血溅五步。 也许只是一些无谓的冲动和浪费的热情,根本不能改变什么,但是这辈子,又有什么东西可珍惜的呢?既已无路可退,那就战吧,挥刀向漫天风雪,只为让鲜花不再凋零。
下篇:想得透,看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