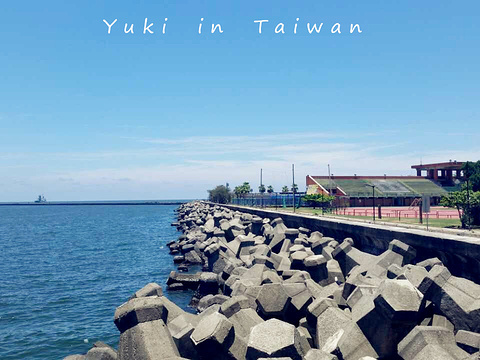讲述故实,博赡贯通,达意妙得
治鲁迅学研究三十余年的孙郁教授最近由商务印书馆印行了其新著《鲁迅与国学》,以十五个专章考察了新知国故间是非取舍,质疑批判中“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鲁迅。讲述故实,博赡贯通,达意妙得,展示出优秀传统文化在鲁迅伟大形象中的底色铺陈和基调渲染之功。
20世纪初期,国学旧学,国故学国粹学,经史之学文献之学,一般语境下是彼此可以通用的。落笔《热风·不懂的音译》,鲁迅推重近十年前的《流沙坠简》,“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要谈国学,他(王国维)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从认识论、知识论和审美论三重审视中拾取鲁迅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做法,孙郁作品第一章即开宗明义。畸形有限与内在欠缺了然于胸,发现珍贵的遗产,重新寻找精神的原态,在双向互动中由旧学而得以染习新知,然后由新知而反观国故,鲁迅不满于将古代经典作为凝固的存在接受过来,从古人世界里发现当下精神,穿越,攀援,他强调的是如何在文脉里发现思想的创造性。鲁迅学有根柢,整理《嵇康集》长达23年之久即是明证。校勘、考证、辑佚,他为之作序跋,并选逸文考、著录考各一卷。说理、发议论,“思想新颖,往往和古时古说反对”,“师心”和“使气”的嵇康阮籍,确乎和鲁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考古知今,考古验今,考古证今,北魏郦道元、宋人陈亮、明代顾炎武一直沿袭着如此文化理念。孙郁在本书中发现鲁迅思想逻辑由章太炎而来,活用老师的学问,又透出老师没有的气息,文章风格也受了老师影响,既深刻警辟,也复杂多变。“章太炎由古逆今,鲁迅则今中含古,各自有创造性的表达”,开启了学生思考的雄浑、想法的跳跃等许多方面,古今互证,念之又念。正如鲁迅《华盖集》《答KS君》《忽然想到》《这个与那个·读经与读史》篇什中点睛之笔与剀切教导:“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野史和杂说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
自称是“学匪派考古学”的鲁迅建立在史学基础的野性思考,偏好从“涂饰太厚,废话太多”的正史之外去寻找另一种可能,于乡邦文献、无名者文字乃至禁书背后窥见生命真迹,又能发现破绽盲点,打开新领域,破除集体遗忘中的虚伪躲闪,让久被压抑的精神蠕活。1933年《南腔北调集·经验》里他不无感慨:“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1934年《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中他更是直抒胸臆:“还不如选几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笔记来印印,倒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
今古、正野话题之余,本书第五章《非儒非孔的理由》中所提及的异同是非,所论定的“在礼教终结地废墟之上,鲁迅诞生”,从文化史角度切入以观鲁迅与孔子,不能不说两人境界的相似。两人最大接近点是在一个传统失范的年代,选择了与流行文化不同的路径。他们“不因苦而退,不因乐而休,超俗的人间情怀与思想境界,值得我们连声赞佩,赞佩”。孙郁主张摆脱对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思想的实用目的和负面看法,打破俗儒暮气,恢复其有趣、自然、人道的温度,立高洁辞章,以古典学研究的精神“得其妙意而用之”。同也不同的孔子和鲁迅,前贤希望克己复礼,以节制方式进入太平之世,而后来者鲁迅则是“在抗争里,独战群魔,其英雄气概何人抵之?”
鲁迅思想的最核心之处乃战士精神,反抗,争斗,多维的挑战者姿态,和形形色色的敌人战,底层意识,平民之态,关注大众,扶持青年,最后一章大书鲁迅钟情、弘扬的墨学精神,苦行隐忍,忘我牺牲,振世救弊。鲁迅从墨子传统墨家价值中打捞出殊为可贵的遗绪亮泽,道德完整性,社会责任感,果敢的行动者,朗健的英雄者,古老精神成为现代思想的一部分,为鲁迅“立人”“改造国民性”之追寻提供了正面、切实的答案和题解。他反感的是古代遗产使一些文人掉进自欺自恋中。他忧心所在是,冲突、争论中读书人“既离民众,渐入颓唐”,走不出暗处盲区,无法于广学博征中求得真义。
鲁迅杂文是中国现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可当丰富的民国别史来读。于传统有吸收继承,又有打破冲决,中外参照,文章新命,“曲笔、冷笔、诗笔等手法,使表达获得了新的活力。”以批判眼光重审旧文明,激活了古老的文脉,重新延续旧文化最为有活力的部分,摄取旧遗产的精华而创造新文化,孙郁先生以鲁迅作为典范样本来照亮当时的语境,“文除百代之弊”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鲁迅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一起在“五四”前后的探索,是“现代知识人自我解放的一次疾走,他们也因此影响了后来的学术、艺术之路,成了中华文明史永远伫立的路标”。《鲁迅与国学》中的深思与洞悉,让我们想起了近百年前茅盾《鲁迅论》中的一句话,鲁迅不肯自认为“战士”或青年的“导师”,“你大概不会反对我称他为‘老孩子’”。民族魂,中国的脊梁,众议自说,他当之无愧。“实际是推翻了许多旧物,廓清了大道,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徐梵澄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时的评价,与新时代孙郁的结论恰似合奏,堪称共鸣。

自序(写给青少年的数学故事(下):几何妙想)书评
现在有不少青少年崇拜明星,我起初对此不是很理解,于是问了一位年轻朋友:“这位明星到底有什么地方吸引你?”这位年轻朋友瞪着一双大眼睛,注视了我好久,最后反问一句:“难道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偶像吗?”我回答说:“我当年喜欢、尊敬的是科学家。”
这段对话虽然简短,却深深地反映了我和一部分年轻人之间的代沟。
在我求学的时代,全国推广了“向科学进军”的活动,祖冲之、门捷列夫、居里夫人等科学家成为我们当年崇拜的人物。那时,大家爱读科普书,如《十万个为什么》《趣味代数学》《趣味几何学》。同时,全国各地举办科学展览,我们也组织科学故事会,这些活动在我们那一代青年人心中种下了科学的种子。 遗憾的是,当年由于种种原因,鲜有国内作家的科普作品。
其实在 1949 年之前,刘薰宇等人写了不少数学科普书。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推动中学生数学竞赛,一些著名的数学家为中学生做讲座。后来,这些讲座的内容被整理成书,并得以出版。这些作品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
在这些科普作品中,最值得推崇的就是华罗庚先生的作品。他写了《从杨辉三角谈起》《从孙子的神奇妙算谈起》等著作, 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华老作品的内容难度的起点往往很低。他常常先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或介绍一种“笨办法”,之后娓娓道来,把数学内容一一讲清楚,最后一个“点睛之笔”,讲明这个问题与高等数学中某个深奥的知识点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华老还会把数学史故事融合到讲座中去,有时还会赋诗一首。他的书成为数学科普读物的精品和典范。
当年我刚参加工作,华老的书让我爱不释手。我那时就想:我也要学习写科普作品。于是,我无论遇到何种困难,多年来仍从不间断地阅读科普书籍。后来,我应出版社之邀开始写作,就一发不可收,写下了《等分圆周漫谈》《1+1=10:漫谈二进制数》《循环小数探秘》《漫谈近似分数》《几何就在你身边》《数学脑袋探秘》等作品。数学科普作品不该总摆出一副“老面孔”,应该适当结合时代的发展。当然,新的数学成果往往很艰深,比起生物、物理等学科,尖端的数学知识更难于传授,但我们还是应该尽力而为。
我在多年前写过一些作品,但随着时间流逝,科学在飞速地发展,如今又出现了很多新的素材。这次出版的《写给青少年的数学故事(上):代数奇思》写给青少年的数学故事(下):几何妙想》两本书,实际上是对之前作品的一次重塑:我修订了一些问题,也补充了一些新内容,目的是再现经典的数学故事,并尽量以读者们能够读得懂的方式,展现新的数学研究成果。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最后,希望大家喜欢数学,热爱数学!
陈永明,2020 年 8 月,时年 80 岁
一个有钱又有才华的豪门富少对一个女子的痴恋
说起对爱情的表达,恐怕最擅长的要数文人。古今中外,为爱情创造出不朽华章的诗人比比皆是。陆游的“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浸润着无限的情缘和无奈;纳兰容若的“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抒发了怀念旧爱的情愫;顾城的“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道出了宁静的心心相印之感……
人类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爱情诗,其中有一部分是为悼念逝去的爱人所作,格外受到世人推崇。比如苏轼的《江城子》里,“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还有英国诗人哈代的《声音》里,“无论遥远还是亲近,再也听不到你。”这些诗作中,诗人借助生者亡者的情感表达来渲染出一种朦胧凄美的意境,使得诗作弥漫着浪漫主义的色彩,生动地表达出对已故妻子的那种超越生死界限的思念,同时也反衬出自己的孤单和凄凉。
《智惠子抄》也是这样一部歌颂爱情、悼念亡妻的作品。这是日本著名雕刻家、画家与诗人高村光太郎四十年来写给妻子漫长的情书。诗集收录了高村光太郎明治四十五年到昭和二十五年所做的作品,记录了光太郎和妻子智惠子从相恋的不安、婚后贫穷又幸福的生活,到智惠子患病仿若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以及决然离去后诗人的一系列生活光影,可以说它是二人的纯爱物语。书中有智惠子发病前两人相思相爱的诗、发病后令人悲伤的诗,以及去世后追忆的诗。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虽然智惠子去世了,却一直活在光太郎的心中,并且不断地升华。
有关智惠子的一生,我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智惠子是一个充满魅力的现代女性。她骑自行车,喝五色酒,还创造艺术。也正是源于此,她得以收获光太郎隽永的爱情。然而光太郎出身豪门世家,他与智惠子的恋情遭到了家里的强烈反对。为了追求理想中的爱情,光太郎毅然与家庭决裂,和智惠子结婚,做了一对清贫却和睦的柴米夫妻。然而幸福的生活没过多久,智惠子便在思考中丧失了自己,得了精神分裂症。而光太郎一边写诗,一边照顾他的妻子七年,直到1938年智惠子去世。
在《智惠子抄》一书中,处处可见光太郎对智惠子深刻浓烈的爱。在他眼中的智惠子是纯真的、完美的:
这些诗作既富有浪漫主义的幻想色彩,又有浓郁的日常生活气息。正是光太郎对自己婚姻感情生活的一段纪念。在这些诗中,光太郎以坦诚无饰的叙事手法和真挚伤感的抒情笔调记录了夫妻相知相恋的甜蜜岁月和悲苦离散。
中国明末清初文学家李渔曾说:“终篇之际,当以媚语摄魂。”所谓“媚语”,即内涵丰富、意蕴深刻的语言。《智惠子抄》无疑属于这种。每一首诗,每一篇文章,都有着深情的开头和精彩的结尾,耐人寻味,给人无限的遐想空间。光太郎在书中表达的,不仅仅是失去妻子的悲恸,还有着对往昔美好岁月的甜蜜回味,令人不胜感慨。
通读《智惠子抄》会发现,光太郎的诗歌既融入了强烈的时代感,又始终保持着浓郁的传统风格。他的诗歌是现实主义的叙事风格、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与现代主义的思想意识三者融合的产物,准确传达了对智惠子魂牵梦绕的思念,使诗歌始终处于一种凄婉柔美的意境之中。
在这部作品中,爱与死是两个紧紧联系的主题,所有诗作都围绕着这两个主题展开。死不仅仅是智惠子的去世,还是爱情幻灭的象征。在《智惠子抄》补遗部分,有几篇散文,真实记录了智惠子患病期间到去世以后光太郎的情感起伏:
这些文字让人感动、感慨、回味无穷。
有人说光太郎的诗缺乏技巧,其实他只是在用和一般诗人不同的技巧在建构他的诗。他的诗是生命在彻底燃烧后自然生成涌现的,是从心底里流淌出来的,所以他的诗就是他的生活,就是他的人生。
情感是诗歌的灵魂,一切言语都是其外在形式或载体,须与其产生共鸣,才能产生感人的效果。对亲情的眷念、爱情的追求、幸福的憧憬,都在《智惠子抄》中得以体现。情真意切的诗作自然能感人至深,散发出永恒的魅力。
下篇:卿本佳人,奈何做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