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研军旅小说的突围路径
■杨 玺 唐 莹 本报记者 傅 强
11月的昆明,阳光煦暖,山茶绽放。由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出版社《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和武警云南省总队政治工作部联合举办的“传承红色基因,抒写强军故事”全军小说笔会于11月10日至15日在武警云南省总队举办。这次笔会是经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批准,继今年6月“诗颂强军新时代”全军诗歌笔会成功举办之后,又一次全军性的文学创作研讨活动。来自全军的老、中、青三代小说作家代表和中国作协领导、文学报刊主编,围绕着军旅小说怎样更好地继承军旅文学优良传统、反映强军兴军新的伟大实践等主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研讨。
拥抱机遇,军旅小说要把推时代脉搏
“军旅小说始终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在文学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当前,人民军队正在经历着革命性历史性的变革。军旅小说创作面临着困难挑战,更迎来了发展的机遇。”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在开幕致辞中开宗明义,英雄主义、家国情怀是军旅小说的精神底色,崇高阳刚、开阔壮美是军旅小说的审美风范。在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中,军旅小说每每都能引领风气之先。无论是回望战争历史,还是聚焦现实生活,都留下了很多堪称经典的精品力作。辉煌的历史,为今天的军旅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厚的资源和参照。
武警云南省总队政治委员王洪斌表示,武警云南省总队铭刻着功勋的红色基因,警营里处处传扬着官兵爱国奉献的英雄故事。小说笔会在这里举办,对于传承红色基因、教育引导广大官兵从军旅小说中感悟英雄精神、打造部队强军文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相信通过这次笔会,军旅小说创作必将出现新的局面。”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创演系主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徐贵祥认为,云南是英雄的土地,有着丰厚的战争文学资源。边防和边疆的火热生活,会带给作家们丰沛的灵感和激情。讲好中国故事,抒写强军故事,是军旅作家的职责和使命。在改革强军的征程上,军旅小说仍然大有可为。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出版社副总编辑刘翎表示,当前,改革强军战略全面实施,这也为军旅小说创作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机遇。祝愿军旅文学才俊们不忘初心、不负众望,积极投身备战打仗第一线,倾听广大官兵心声,守望军旅生活现场,以冲锋的战斗姿态书写强军故事,用真诚的劳动和创造性的写作,生动记录伟大强军实践。
开幕式上的精彩发言引发与会代表强烈共鸣。作家代表董夏青青表示,青年军旅作家要深入探寻脚下土地的历史和文化,关注世界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大势,尤其要聚焦改革强军一线的火热生活。没有这种关注和聚焦,写作就会脱离实际、浮泛虚空、缺少力量。强军新时代给军旅小说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问题,我们要用切入时代脉搏的崭新创作实践作答。
“跟老一代军旅作家相比,当下的青年作家还要加强学习,持续成长。”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朱向前教授通过分析徐怀中、朱秀海等军旅作家的最新创作,表达了作家需要终身学习、终身成长的观点,对“新生代”军旅作家的成长寄予厚望。国防大学教授乔良在发言中强调,年轻的军旅作家要在小说技巧和形式方面多下些功夫,只有叙事的基本功扎实了,才能游刃有余地表达自己的情怀和思想。
裘山山、柳建伟、陈怀国、马晓丽、衣向东、温亚军、陶纯、徐可、孔令燕、陈东捷、钟红明、王大亮、石钟山、刘起伦、陈可非、郑润良等代表结合青年军旅作家的小说文本,从作家、评论家和编辑的视角出发,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我拿到的作品,题材和素材都很好,但是作者把握生活的能力还有很大欠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衣向东的点评直言不讳,辣味十足。缺乏新意、主题不明确、表达不到位、文学素养不足、好题材写不好,是青年作家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论坛上,大家围绕问题各抒己见,认真点评,意见尖锐,直指要害,现场气氛热烈活跃。
与火热的军旅现实生活相比,当下的军旅小说创作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滞后现象,无论是在题材幅面的宽广度,还是对新时代高素质军人形象的塑造方面,都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讨论结束后,《解放军文艺》副编审文清丽对记者说:“年轻作者集中听到这么多批评的声音,可能心里不太舒服,但这是在创作的道路上必须接受的刺激;好好消化吸收,认真领悟专家们提出的意见建议,对他们未来的创作具有重要的价值。”
当下的军旅小说创作,好像跟外面的文学世界隔离起来了。这种脱节既有题材自身的局限,更多的还是源于作家自身文学观念和叙事方法的陈旧。在军事题材小说主题论坛上,大家围绕“军事小说如何聚焦强军实践,探寻突围路径”等主题进行了研讨。
代表们普遍认为,现在的青年作家大都很焦灼、焦虑,对军旅小说创作也存在着一些困惑和瓶颈。英雄叙事并非是概念化的空洞概念,而是一座题材和精神的富矿,需要持续探索和深入挖掘。近年来军旅小说创作也存在着老气横秋、同质化、可读性差的现象。青年作家应该以一种充满朝气的崭新姿态,聚焦强军兴军,获得新的生活和创作资源。
青年军旅作家王凯、李骏、西元、丰杰、弓艳、周鸣、赵宇、高满航、朱旻鸢、舒笠桦、高密、杜晨等结合自己的军旅生活和创作实践谈到,军旅小说创作应该从“小我”跳脱,向外拓展,创造更为宏阔的军旅经验;在题材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上应当进一步开掘创新,使作品具有更加多样的风格和面相。
卢一萍、王棵、王甜、曾剑、孔立文、王玉珏、言九鼎等认为,虽然脱掉了军装,但是军旅生活和经验依然是自己最重要的写作资源。从军营到地方,新的身份和经历,使得自身的创作具有了新的视角和可能性。希望能有更多的渠道和机会,了解熟悉正在进行时的军旅生活,为军旅小说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解放军文艺》主编姜念光在总结发言中谈到,军旅小说有自身独特的坐标系,作家们既要有稳定的世界观、价值观,又要有自己的文学观和美学观,还要努力建构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尤其要强化自身的军事理论和科技素养,只有这样,才能有足够的底气和实力去跟踪表现改革强军的新时代,真正使得军旅小说振兴突围。
笔会期间,主办方还举办了改稿辅导、专题讲座、参观采风、文艺演出等活动,以期发现和培养年轻的创作骨干,为推动军旅文学的发展和忠实记录伟大强军新时代蓄力鼓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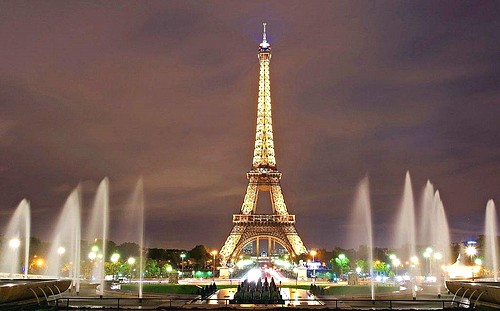
茅盾系列之军旅作家柳建伟:“时代三部曲”用文学传承红色血脉反映时代精神
e线荐读
柳建伟(1963‐),河南南阳镇平县人。中国作协全委会主席团委员。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时代三部曲”(《北方城郭》《突出重围》《英雄时代》)、《惊涛骇浪》,长篇报告文学《红太阳 白太阳》《日出东方》等。《英雄时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以长篇小说《北方城郭》《突出重围》《英雄时代》组成的“时代三部曲”,成为了世纪之交中国文坛的一道靓丽风景。这三部作品各有千秋,从三个不同维度描绘出作家柳建伟的立体呈现。
《北方城郭》写得最扎实饱满,元气淋漓。
《突出重围》最具前瞻性地展示了新世纪的中国军队,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英雄时代》以题材取胜,并最终摘取了中国文学至高荣誉第6届茅盾文学奖。
震撼人心的《北方城郭》作为柳建伟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曾被出版界誉为能与《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并提的现实主义巨构。小说以豫西南龙泉县城为中心展开,在四十余年的时间跨度内,对当代中国城乡现实进行了全方位、多层面的描画。小说直面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深刻地描绘了社会转型期中国人的生存境况,塑造了李金堂、刘清松、欧阳洪梅、林苟生、申玉豹等众多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显示出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强大生命力。
李金堂这个人物的塑造被认为是小说中最出彩的,作者成功地将人物的多面性展现在读者面前。每人心中的李金堂都应该不尽相同,你可以认为他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土皇帝,也可以认为他是雄霸一方的伟丈夫。不过,一个词绝对不足以形容他,精于权术,政治铁腕,铁汉柔情,心思缜密,经验老到,这些都可以做这个人物的注解,但或许还不够。
《突出重围》是一部反映当下我国军队建设情况的现实主义力作。小说以作家的军旅生活体验和现实主义创作倾向为基础,成功地塑造了像范荚明、朱海鹏、方英达等一系列当代军人的新形象。
这是一部着力描写人物群像的作品,几十个人物分布在从普通士兵到大军区司令的广大“空间”里,错落有致、浓淡相宜。方英达、朱海鹏、范英明等人物形象富有独创性。这还是一部具有“盛世危言”品格的忧患之作,体现了中国作家对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认识水平和表达能力,呈现出的沉郁、激越的美学风范,暗含了转型期的时代精神。在接受方面称得上雅俗共赏的作品,其结构完整、情节丰富。作品中虽然没有出现堪与李金堂比肩的典型人物,却以完全不同的艺术品格和文学景观,显示出了作者磅礡的创造力。
《英雄时代》该小说大开大合,以一个红色家族的几个主要人物在北京和西南中心城市的命运沉浮为主线,描绘世纪之交社会变迁的壮阔图景,既写出物质狂欢时代物欲横流对正常秩序的破坏,也写出时代英杰和广大人民群众对理想、信仰的坚守,对丑恶的抗争和对美好未来的希冀。该小说结构宏大,采用直面现实的叙事手法,广泛呈现了当代中国的经济生活场景。
小说以高干子弟陆承伟、史天雄两兄弟在城市改革深化的关键时刻作出的不同人生选择为故事线索,表现他们不同的性格、气质和精神境界,提出了攸关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性改善的诸多法制、伦理问题。环绕着陆承伟、史天雄的对峙、冲突,作者展开了从京城高干家庭生活到内地边远城市的普通女工的生存挣扎等多层次的生活场景。
在柳建伟的“时代三部曲”中,可以领略到当下中国从乡村到都市、从“地方”到军营的各色风景。据他自述,《英雄时代》其实与《北方城郭》和《突出重围》的内在精神相一致,三部作品合成《时代三部曲》,基本上能概略表达出对当下中国的基本判断。
军旅作家汪瑞:用文字展现灵魂深处的惊涛骇浪
汪瑞创作的反映西藏阿里边防的散文,是岁月留在她心灵中深刻的印迹。也许是因为我多次在拉萨向高耸入云的阿里高原遥望,我很乐意为她这本散文集写几句话。
此前,我读过她早些年出版的散文集《当兵走阿里》,爱得渗透心肺,难以放下。汪瑞笔下的阿里边防战士,和我熟知的青藏线官兵,这二者的形象,总是不由自主地在我脑海和眼前重叠。他们让我敬重,是我学习的榜样。
独特的土地造就独特的文化,也造就了真实而独特的作家。多年来,我将汪瑞视为我的作家朋友和榜样,尽管至今我和她无缘见面。这又何妨,我们的笔是相连的,挚爱西藏的心是相通的。
我长久地盯着书名上“界碑”二字,眼前反复呈现着汪瑞笔下描绘的那些拥高山入怀、挺胸收腹站立的西藏边防军人的形象。他们握枪的指缝间以及凝视远方的瞳仁里,都放射出锋芒毕露的美。可是,有多少人会知道他们是在怎样的环境里守卫国门?汪瑞写道:“这里孤寂而苍凉,这里低氧、低温、低气压,所以,它被称为地球的第三极。但这里的空气却并不因为诸多的低而轻飘,反而因此具有了沉甸甸的分量,仿佛一块无边无沿的巨大石板重重压下来,压得大地几乎窒息”“山腹中,层层叠叠的雪山像一片片巨大无比的肥硕花瓣,有力地簇拥着,紧紧抱成团……雪山中的哨卡常常被许多人称作‘雪域孤岛’。山脉边缘,花瓣渐渐变得松散,银白渐渐融淡,一点点显出山岩青黑的底色,直到渐变成沙漠的黄色。”
我之所以引用这段文字,只是想让未去过阿里边防,或还没有机会读汪瑞散文的人知道,我们可敬可爱的边防军人是在多少人意想不到的艰苦、荒凉的环境里,日夜守卫着祖国的神圣疆土。这里甚至终年连一棵草、一块鸟粪也见不到,却有他们站岗巡逻、执勤放哨的身影。
汪瑞的散文试图通过这种艰辛而漫长的历练,真实再现边防军人坚韧的生命力、温暖的人性光芒和他们执著于理想信念的人生经历。许多战士站在这样的哨位上时只有18岁,他们一站就是数年。对于他们而言,此处哨位让18岁成为他们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年龄,这段经历让他们体味到铭刻于生命中的尊严。高原上的生活也许有时并不完美,但生命却能拥有不可战胜的力量!
汪瑞的散文是从生命深处自然生长出来的文字。她的本职工作是阿里边防的一位医务人员,数十年军旅经历让她从普通护士成长为优秀的护士长和一位军旅作家。军人和作家的双重身份让她的许多散文具有强烈的现场感,让我们读起来如身临其境,荡气回肠。我想,只有把自己置身于边防一线,融入守卫界碑的边防官兵中,对他们的情怀感同身受,对他们的生活切身体会,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同苦同难才有同乐,而这其中的“难”,比苦更涩、更险,也更刻骨铭心。这让我想起了诗人公刘在给一位画家的信中提到,画家的心里要有“受苦人”。他的话道出了一个真理,文学艺术家若是在生活中不经历磨难,没有曲折、没有黯淡、没有饥饿、没有寂寞,也就不会有深刻的思想,不会有丰沛的理想。把个人经受的苦难,当成前行的动力,这既饱含着文艺创作者们对国家、对民族的深沉情感,也蕴含着他们对劳苦大众热忱的理解与挚爱。
文学艺术创作是一个充满艰辛又满含喜悦的历程。汪瑞经过长期痛苦而快乐的历练,已成为阿里这片皑皑冰雪高原上的一粒冰晶,折射出璀璨而温暖的光芒。她用文字展现灵魂深处的惊涛骇浪,以深入骨髓的热爱与阿里高原接轨。
汪瑞多年来在阿里的非凡经历,让这片异常艰苦的边疆热土变成她的第二故乡。从某种程度上说,或许将她的作品称为乡土文学也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她的军旅情怀和在军营的历练,使她的作品在传统乡土文学基础上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更深刻的情感表达。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我读汪瑞散文后的印象,那便是:对“根”的留恋和对“家”的不舍。
我真诚期待,她在阿里好好地生活,畅快地写作!
相关资讯
军旅作家王凯《绿沙漠》出版,书写西部沙漠驻防生活
澎湃,澎湃新闻,澎湃新闻网,新闻与思想,澎湃是植根于中国上海的时政思想类互联网平台,以最活跃的原创新闻与最冷静的思想分析为两翼,是互联网技术创新与新闻价值传承的结合体,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