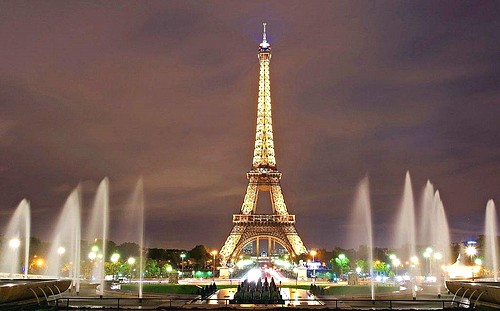看看艺术家笔下的母亲肖像分享艺术乐趣
《40位伟大艺术家为母亲所绘肖像》近日在英国出版,它独树一帜地将梵·高、塞尚、毕加索等40位伟大艺术家为其母亲所绘的肖像画巧妙编排在一起,讲述了诸多艺术创作的有趣故事。5月10日是母亲节,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节日前夕,让我们走近这些伟大艺术家和他们笔下著名的母亲肖像,分享其不凡的艺术乐趣。
一些伟大艺术家最经典的作品,往往是他们的母亲肖像。在艺术史上,许多大师只画母亲而不画父亲。其中,高更将母亲的长相改得具有异域情调,梵·高凭记忆给母亲画上绿眸子。现实中,母亲造就了孩子,但在绘画中,却是孩子造就了母亲,从而使这些经典的肖像绘画作品,呈现出独树一帜的风格。
亲情派
惠斯勒母亲肖像 亲情洋溢
著名画家惠斯勒最有名的肖像画就是这幅《惠斯勒的母亲》:67岁的母亲侧脸端坐,脚踩在脚凳上,目光凝视前方,很难揣测在想什么。据说,惠斯勒那天在等模特,但模特没能到达,于是妈妈同意代替模特坐在那儿让儿子作画。正是这种血缘情感上的密切关系,使母亲常成为惠斯勒描写的对象,也只有母亲,才愿意这样为孩子静静不动数小时。相对来说,画家笔下的父亲肖像却很少,因为男人为生计忙碌,在家庭的需求中常常是缺席的。在母亲看来,摆出姿势让孩子作画,是表达母爱的一种很普通的方式。因此,惠斯勒的妈妈在给亲人的信中说:“哇,当我亲爱的儿子突然欢呼‘哦,妈妈,我完成了,它多么美啊!’时,我真是由衷地感到高兴。接着,他会因为那幅画亲吻我。”
逼真派
安格尔母亲肖像 真实传神
这些艺术大师的母亲肖像通常强调真实感,而非单纯追求美感,从而使母亲形象更趋逼真。画家安格尔所绘的母亲肖像是1814年他母亲安妮去罗马探望他时所作,画家让肖像充满了传神逼真的特色,基于他内心希望母亲看上去像能从画布上走下来。站在这幅感人的画作前,这种传递出的爱意表露无遗,母亲对儿子的爱和儿子对母亲的爱,都交融在画面里。而画家朱尔斯·巴斯蒂昂·勒帕热所绘的母亲的肖像,则非常美丽,真实得近乎一幅照片。事实上,勒帕热本来就是照相术的积极追随者。这些母亲在她们儿子的笔下,因真实而更显得“完整”。
高更母亲肖像 情调独特
一些艺术家擅用自己的画来修补缺憾的现实,高更一生将大量的精力倾注于描绘外国情调上。高更所绘的母亲肖像,来自于他母亲年轻时的一幅照片。他故意将母亲的面部特征进行夸张,嘴唇画得更厚,鼻子画得更宽,这也许是为了强调他母亲身上的西班牙异域血统。梵·高同样是根据母亲的照片来画母亲的肖像,但他嫌原始的黑白照片太单调,所以按照记忆来描绘心中的母亲形象。在人们看到的画面中,他的母亲有着一双温暖而美丽的草绿色眸子,映衬着完美的肌肤,画面洋溢着淡淡的忧伤和温馨。
印象派
卡萨特母亲肖像 充满奇幻
还有一些著名画家则展示的是生活悠闲而富裕的母亲形象。几乎从不画肖像画的塞尚,却画了他的母亲和妹妹玛丽日常生活的常态,弹钢琴、做针线。他的父亲,一位不赞成儿子绘画的银行家,本来也被画在画中右边的椅子上,但后来被用颜料涂掉了。美国印象派画家玛丽·卡萨特为母亲所绘的肖像最引人注目。她深受日本传统绘画影响,用一种完全无视西方艺术大师们制定的规则的方式为母亲画像,其绘画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现代意识,极具装饰性和深刻的主观色彩。整幅母亲肖像体现了强烈的光影效果,充满了奇幻感。
悲情派
霍克尼母亲肖像 孤独绝望
画家们迥异的生活境遇和成长经历,常常在他们的母亲肖像中表露无遗。在画作《我的母亲,博尔顿修道院,约克郡,1982年11月》中,画家大卫·霍克尼用一种照片拼贴的方式描绘了一个穿着廉价雨衣的美国女人,她看起来非常孤独。画面一角,画家穿着昂贵皮鞋的脚故意被画入画中。画家想用这种独特的绘画方式体现他和母亲的困境,以及在生活中面临的绝望,霍克尼甚至在他父亲的葬礼上画母亲的肖像。此外,著名画家迪雷尔也为他的母亲画过肖像,他希望以此来反映一种残酷而诚实的生命过程——母亲15岁结婚,生了18个孩子,却只有3个活了下来。在母亲死前几个月,迪雷尔还为她画过肖像。“甚至最细微的皱纹和静脉也绝不能忽视。”通过这位母亲的脸,我们可以理解她曾过着怎样的生活。(许珍)

充满奇幻色彩的水彩画世界
在沃特斯穆什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知的好奇。他的画作中充满了色彩和活力,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场景都仿佛在跳跃、在呼吸。他的画笔下的世界,充满了奇幻的色彩,仿佛是一个童话故事的世界,同时又带有深深的现实意味。
这种深深的现实感,来自于他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和深刻理解。他的作品中,你可以看到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可以看到人类的欢乐和悲伤,可以看到生活中的形形色色。这些都是他对生活的理解,是他用画笔表达出来的生活哲学。
亚历山大·沃特斯穆什(Alexander Votsmush),1967年出生于俄罗斯鄂木斯克,1987年毕业于克里米亚艺术学院,1991年杰拉西莫夫电影学院学习动画课程。1998,他参加了苏富比拍卖行——“艺术链接”(特拉维夫)展出,展出的作品全部售出,自此一举成名。
走进亚历山大·沃特斯穆什的艺术世界,你会发现自己仿佛踏入了一部生动的动画片。他的每一幅作品,都像一个鲜活的故事,细致入微的细节让人仿佛听见了他们的对话,看见了他们的动态。他的画笔似乎拥有魔法,将梦幻与现实、理想与生活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
的作品也充满了梦幻和奇幻的元素,这些元素源于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对未来的期待。他的画作中,你可以看到天马行空的想象,可以看到未来世界的模样,可以看到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
亚历山大·沃特斯穆什的作品,是他对世界的理解,是他对生活的赞美,是他对未来的期待。他的画作,仿佛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让人们在欣赏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他的情感和思想。他的作品,是他的心灵之窗,让人们看到他的内心世界,看到他的梦想和希望。
祝耕夫的奇幻世界|漫画家的秘密
“漫画家的秘密”是由快看漫画独家策划的一档文字栏目,旨在记录中国漫画作者的成长,见证中国原创漫画力量的壮大。第八期我们和《人类进化论》的作者祝耕夫聊了聊。
你看过祝耕夫的漫画吗?那是一种适合在夏天的夜晚,一个人躲在被窝里,打开空调阅读的漫画。
在一个或写实或虚构的平行世界中,剧情大抵是奇幻猎奇的,你可以跟随主角的步伐缓缓推进,抽丝剥茧,一步步接近内核。最后,真相大白,酣畅淋漓。
然后,你拉开窗帘,看着后半夜的天空,陷入沉思。
这是祝耕夫想要的,他理解的漫画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消遣,而是一种带有思考的表达。而所有的思考,都指向人性本身。
生于1989年的祝耕夫很早就与漫画结缘。在2012年出版的《漫路》一书中,他用黑色幽默的笔触写道:“从小喜欢漫画,初中开始自己的漫画创作,大部分灵感迸发在课堂……我一直以为漫画只是爱好,但也曾经有过做漫画家的梦想,无奈理想太过丰满,现实太过骨感。有过挫折,受过欺骗,也获得成长。无论怎样,自己从未放弃漫画,因为它已经成为了我身体的一部分。”
2015年,快看刚创办不久,安妮联系到祝耕夫,希望他来快看连载。“而且安妮是亲自打电话给我,我们后来还在北京见过面,还请我吃饭,觉得安妮和快看都很有诚意,就和快看签约了。”祝耕夫早期作品以恐怖漫画为主,之后进一步扩展为一个更为恢弘的奇幻世界。
在《人类进化论》中,祝耕夫讲了《沉默盒》、《迷雾岛》、《玩偶工厂》、《狐的报恩》、《恋人小岛》、《渔村》、《雪女》、《新人类》八个故事,包罗万象。
《沉默盒》是一个都市传说类型的故事,它虚构了一只在背负罪责之人中流转的神秘盒子,能看到这只盒子的都是曾经犯下罪孽却逃过法律制裁的人。因为盒子的诅咒,他们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正义重新得到伸张。
在漫画故事中,自卑的幼杰因为暗恋同学小浅,策划了一场强暴案,试图摧毁小浅的自信毁掉她,从而得到她;有着虐杀爱好的阿忠残忍杀害了一个哑巴小女孩,并抛尸大海,但因为未满12岁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他们最终都倒在了沉默盒的诅咒之下。
看似荒诞故事的背后是朴素的道德审判。
《新人类》则借助一个科幻故事的外衣讲述了一个社会故事。故事发生在未来,由于战争、核武器、大气层破坏、资源枯竭、自然灾害等一系列原因,地球变得不再宜居,各国失业率暴增,社会不稳定性增加。为了带给人类新的希望,政府宣布将派出一支小队前往一个新的适宜人类居住的星球,进而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故事……
和郝景芳的《北京折叠》一样,这个故事同样在科幻的外衣下隐藏着对于人类社会的思考,属于软科幻范畴。这里就不做剧透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移步快看漫画app一睹为快。
不过,如果因为恐怖漫画出色就此把祝耕夫定义为一个恐怖漫画家,可就犯了形而上的错误。
祝耕夫厌恶标签论,对他而言,创作者拥有无限的可能:“我更喜欢多元化的创作,我不喜欢别人用一个个的标签贴在一个人身上,例如‘ 恐怖漫画家’,其实看过我早期作品的人都知道,我有很多漫画并不是恐怖的。而我今后也不可能一直画恐怖漫画,今后我也会画各种各样类型的漫画,我更希望自己成为一名漫画家,而不是一名画‘ 某某的漫画家 ’。”
这不,在即将上新的新作中,祝耕夫就尝试了一把温情路线。不过由于疫情原因,老家武汉的他耽搁了一阵子,直到5月回到杭州才算重回正轨。他在微博上写道:“没有画画的板子,要回到工作室才能开始画,现在只能在草稿本上画画分镜”。
“我想用好作品去触碰人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是祝耕夫在新作筹备期所展现出的野心。这部新漫画,叫做《漫画一生》。
这部漫画的标题也是祝耕夫个人价值观的写照。他曾经问过别人“如果你有一天突然有一个亿了你会做什么”的问题,大部分人的答案都是要买豪宅环游世界不工作之类的回答。
然后他思考了一会,说道: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买一间豪宅,然后坐在里面继续画漫画。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做着自己不喜欢做的工作,一个人的工作又刚好是自己喜欢做的事,那这个人大概就是这世上很幸福的人了吧。我有时分不清我是很幸运还是很努力,我现在就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我没有一个亿,我会画漫画,我有了一个亿,我还是会继续画漫画。
但是,越是热爱的人,越是能够清醒地看到乐观背后的不足。祝耕夫始终抱着最坏的心态去做一些准备:“现在流行的作品基本都是以画风美型为主,故事就比较模板化,好多作品感觉乍一看都是差不多的类型;漫画平台的作品类型也有些单一化了,一个漫画平台如果要吸引到各个领域的受众群,还是要让作品多元化一些……不要去谈如何把一个行业做到多么大,多么国际化,现在还有很多创作者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让各个平台先保持盈利,让文化支柱先稳住,这样才能让支柱下的创作者继续输出自己的结晶。”
不过,在面对日益增多的年轻漫画家,面对这些青涩和热情的面孔时,祝耕夫还是收起了悲观,充满希冀,说出心里话:“很多东西都是一时的,画风也好,人设也好,现在是淘汰更新很快速的时代,如果你真的想一直画下去,就还是想着如何把故事讲好,如何让自己的故事打动人,让读者们久久都难以释怀,这样的作品才是能经久不衰的。”
对于祝耕夫和中国漫画来说,这样的征程或许才刚刚开始。
相关资讯
新西兰的萤火虫溶洞简直是画家笔下的魔幻世界
相信许多喜爱电影的人都知道,新西兰是著名魔幻电影《指环王》三部曲的重要取景地。 比如,《指环王》中的霍比特人小镇夏尔(The Shire),取景地就在新西兰的惠灵顿 洛汗王国首都的埃多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