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禁毁言情小说
《中国古代禁毁言情小说-隋炀帝艳史 风流和尚 桃花扇》为《中国古代禁毁言情小说文库》之第十三卷,收入明代长篇章回小说《隋炀帝艳史》及清代小说《风流和尚》、《...
《空空幻》: 清道光年间著名情爱小说,主要情节由丑陋男子艳羡风情所产生的“不安分”的性幻想构成。书中鄙弃世俗情爱价值,大写喜新而不厌旧的花痴型男子走马灯般更...
《中国古代禁毁言情小说-玉楼春 八美图 情梦柝》为《中国古代禁毁言情小说文库》之第十八卷,收入《玉楼春》、《八美图》、《情梦柝》三部清代章回小说。 《玉楼春...
《欢喜冤家》:又名《艳镜》、《欢喜奇观》,不题撰人。全书24回,每回演一个故事,集中描写了各种曲折奇异的婚姻悲喜剧,生动展示了明代社会形形色色的人情世态既有...
醋葫芦它是继《金瓶梅》之后“艳情小说”中最具风格的一部佳作。是一部反映封建专制下,人们渴求释放积怨,追求自由的典范小說。元末明初的社会大动荡,摧残、扭曲着社...
《中国古代禁毁言情小说-归莲梦 隔帘花影》为《中国古代禁毁言情小说文库》之第十七卷,收入《归莲梦》、《隔帘花影》二部清代章回小说。 《归莲梦》全称《新镌绣像...
《金石缘》讲述了江南苏州府有位名叫金桂号彦庵的少年解元,生一子名金玉字云程,一女名元姑。阊门外有富户林旺,其长女爱珠,虽然才貌颇佳,但赋性轻浮;其次女素珠相...
《绮楼重梦》书接《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宝玉转世为宝钗之子,名唤小钰。黛玉投生史湘云家,取名舜华。二人自小同贾兰之女优昙、曼殊、文鸳于邢岫烟处读书,情意日笃...
《五美缘》书叙大明正德年间礼部尚书冯旭,风流倜傥,喜获五美相伴,万种风情,百般欢畅,正是:云鬃蓬松起战场,花园锦簇布刀枪。 《山水情》讲述了卫旭霞与邬素琼的...
《锦绣衣》:清初文人创作多回拟话本, 以戏为名,共收两戏。 第一戏:换嫁衣。两卷,卷一、二。每卷三回。六回相连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 第二戏:移绣谱。接第一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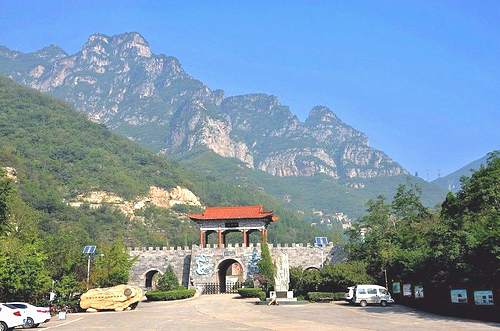
论中国古代小说的抒情色彩
中国古代小说以叙事为基本文体特征,尤其是源于民间“说话”伎艺的白话小说,但古代小说家讲故事的目的则各自不同。有的是为了娱乐消闲,如明嘉靖间洪楩所编话本小说集《清平山堂话本》分为“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闷”“醒梦”六集,其编撰目的不言而喻。有的是为了教化劝导,移风易俗,如秉持“情教”“适俗”“导愚”小说观的冯梦龙编撰“三言”,就意在“喻世”“警世”“醒世”;其他话本小说集像《型世言》《清夜钟》《醉醒石》等,长篇小说如《歧路灯》《醒世姻缘传》等,仅从小说题目即可相见其劝善惩恶的教化功能。当然有的小说为更好地实现劝化效果,往往寓教于乐,如杜纲《娱目醒心编》即属此类。有的小说则是小说家炫学逞才的产物,如号称“四大才学小说”的《蟫史》《燕山外史》《野叟曝言》《镜花缘》。值得注意的是,文人叙事绝非单纯地为叙事而叙事,一般都有情志寄托,也即刘熙载《艺概·文概》所谓“寓情”,纵观中国古代小说史,凡经典之作大多具有较强的抒情色彩。对此,学术界往往因过分重视古代小说的故事性而忽视了抒情性这一中国古典小说的显著民族特色。
就文言小说而言,其文体特征深受史传文学影响,而作为史传文学代表作的《史记》被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誉为“无韵之《离骚》”,就是强调其强烈的抒情色彩。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作家很好地继承了这一抒情传统,如《搜神记》卷十六“紫玉与韩重”写吴王夫差小女紫玉与韩重的爱情悲剧,其中紫玉所吟歌诗情调凄婉,使故事极具艺术感染力。又如《续齐谐记》中“赵文韶”“王敬伯”写人神(鬼)之恋,其中男女弹琴歌吟,凄清婉丽,也赋予小说以浓郁的抒情意味。
在某种意义上说,抒情性是促成中国古代小说文体走向独立的重要因素。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独立,恰如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所言,它“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而“诗笔”即指唐传奇小说浓郁的抒情色彩。洪迈《唐人说荟·凡例》称“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他将唐传奇与唐诗相提并论,也是强调其鲜明的抒情特质。明桃源居士更是将唐人小说的抒情性溯源至楚骚抒情传统,称《楚辞》之后,唐人以其“奇宕不常之气,钟而为诗律,为小说”,言外之意,唐人小说与诗歌一样承载着作者的情感心志。毕竟,唐传奇作家大多为诗人,他们往往以诗性思维叙事写人,如《枕中记》《任氏传》作者沈既济在《任氏传》中即宣称其小说创作是为“传要妙之情”。再如,沈亚之的《湘中怨解》《秦梦记》《感异记》皆为典型的“楚调小说”,它们情节淡薄,不以故事性见长,而是通过穿插《湘中怨》《光风词》之类极富感伤色彩的楚歌来酝酿凄美迷离的情调,着意渲染一种隽永绵长、哀感顽艳的情绪。清人所编《唐代丛书》《唐人说荟》在收录《湘中怨解》的同时并附上《湘君》《湘夫人》,也意在强调这篇小说浓郁的抒情特征。
唐传奇之后,作为中国古体小说第二座高峰的《聊斋志异》也富于抒情色彩。按照蒲松龄《聊斋自志》的说法,其小说是“寄托如此,亦足悲矣”的“孤愤之书”,这在大多数小说篇尾的“异史氏曰”中得到充分体现。在《聊斋志异》写作过程中,蒲松龄《寄孙树百》以“怀人中夜悲天问,又复高歌续楚词”来表达自己的写作心境,显然,抒发胸中磊块是其写怪志异的重要心理动机。纪昀门人盛时彦在《姑妄听之跋》中称纪昀将《聊斋志异》视为“才子之笔”,而把自己的《阅微草堂笔记》定性为“著书者之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他们都认为《聊斋志异》与唐传奇小说的抒情传统一脉相承。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源自宋元以来的“说话”伎艺,为迎合读者的审美趣味,故事性乃其第一要务,但随着话本小说与章回小说的文人化,其主体抒发色彩亦渐趋显著。如《三国演义》虽属世代累积型作品,但中国古代小说评点融评、改于一体的批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赋予评点者以“第二作者”身份,因此《三国演义》最流行的版本毛评本已属文人小说,具有了鲜明的抒情色彩,其卷首《临江仙》(滚滚滚长江东逝水)一词即为全书奠定了悲怆的感情基调。
文人独创型作品的抒情性更为突出。如作为明遗民,陈忱对屈原及其楚辞作品产生了强烈共鸣,作有《九歌》的他除通过所在的惊隐诗社奉祀屈原外,更是有意识地将楚骚抒情传统引入《水浒后传》,他在该小说序中谈及自己的创作动机,自叹“穷愁潦倒,满腹牢骚,胸中块磊,无酒可浇,故借此残局而著成之”,为此他声称自己的这部小说深得“《离骚》之哀”。确实,《水浒后传》乃陈忱抒发其遗民之悲与故国之思的“泄愤之书”。因穷蹙不遇而以小说抒怀者还包括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作家,像天花藏主人《平山冷燕序》所谓“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佩蘅子《吴江雪》第九回所谓“英雄失志,狂歌当泣,嬉笑怒骂,不过借来抒写自己这一腔块磊不平之气”,都是自道其“发愤著书”的创作动机。盛行于晚清民初的“哀情小说”更是以情味醇厚见称于时,徐枕亚在为李定夷《茜窗泪影》作序时称“欢娱之词难工,愁苦之音易好,诗文如是,小说亦然”,他对这部小说的抒情性予以高度赞赏;而他自己的《玉梨魂》也因抒情色彩浓郁而被盛桨《与徐枕亚书》誉为“以伤心人而奏伤心曲”的“再续《离骚》”之作,其《雪鸿泪史》更是“哀怨缠绵,凄清悱恻”(俞长源《〈雪鸿泪史〉序》)。
一些小说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往往带有明显的自况意味,此时其主体抒发意识最为强烈,自然小说的抒情色彩也十分浓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曹雪芹的《红楼梦》。曹雪芹将自己的人生态度融注于宝玉这一形象之中,藉此抒发自己的悲剧人生感受,他师法的正是楚骚抒情传统。在《红楼梦》第七十八回,曹雪芹借宝玉之口声称自己要“远师楚人”,为此他将小说写成了一部彻头彻尾、蕴含多重悲剧意蕴的大悲剧。难怪脂砚斋在甲戌本第一回批中称赞《红楼梦》为“《离骚》之亚”,刘鹗在其《老残游记自序》中也认为“曹雪芹寄哭于《红楼梦》”,这都是对其浓郁抒情色彩的高度肯定。再如,魏秀仁在《花月痕》中以怀才不遇、穷困潦倒的韦痴珠自况,谢章铤《魏子安墓志铭》称魏秀仁因不遇于时,故其“肮脏抑郁之气无可抒发,因循为稗官小说,托于儿女子之私”,就是认为作者通过韦痴珠与刘秋痕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来抒发内心之愤懑。
质言之,我们在关注中国古代小说的故事性、娱乐性的同时,不应忽视作为其民族特色的抒情性。对于小说抒情意味所产生的的艺术效果,郁达夫《我承认是“失败了”》有着极为精到的说明:“历来我持以批评作品的好坏的标准,是‘情调’两字。只教一篇作品,能够酿出一种‘情调’来,使读者受了这‘情调’的感染,能够很切实的感着这作品的‘氛围气’。”以此审视那些具有浓郁抒情色彩的中国古代小说,也极具启发意义。(陈才训)
中国古代九大禁书,每一本都让人看得脸红心跳
,很多伟大人物说了,书籍是通向彼岸的一叶扁舟,所以才留下了“开卷有益”的话!
但是,在某些人看来,书籍也可能会变副面孔,成为毒害思想、蛊惑人心的“毒草”。
是“毒草”,当然就要铲除,于是就有了
毫不讳言,有书籍的地方就会有审查。
中国很注重文明传承,书籍的体量自然是浩如烟海,偏偏中国历史上,大一统是主流,除了政治和军事,连思想也追求铁板一块,所以就有了很多
,毕竟人们在社会中,是需要伦理道理的,这类书籍的流行肯定有伤风化。
此外,和色情类书籍在数量上旗鼓相当的,就是威权统治下的
出于钳制思想的目的,当权者常会害怕如细菌一般的文字和疾病一般的书籍,比如有名的
靠世俗权威禁止并不能根绝这些禁书的传播,就像曾经被禁止的火种一样,它们中的一部分不仅经过重重审查、销毁后得以幸存,甚至在后人的不断阅读、流传中成为了经典。
有哪些经典是因为被禁,反而成为经典的呢?它又是为何被禁的呢?
中国古代早就有禁书的政策,自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有“焚书坑儒”的事件,那个时代也没有所谓的色情小说,那被禁的还有什么书呢?
皇帝最担心什么?毫无疑问是权力的丧失。
秦始皇在位的时候,就有“祖龙死而地分”的说法,所以秦始皇找了个名叫祖龙的人给杀掉了;又有谶语说:“亡秦者胡也”,这才有了秦始皇命令蒙恬北击匈奴。
等到纸张和印刷普及后,这类谶语被编成了书籍,就比如说,这类书籍对于统治来说,是很不稳定的因素,总有好事者会利用谶纬之说来煽动民众,发动起义。
统治者除了不让民间传播不利于自己的书籍外,还禁止将帝王之术传入民间,某些书籍是官方垄断。
是有名的天下第一禁书,为战国商鞅所作,只有历代的皇帝或者太子才能读到,是用来帮助皇帝治理天下的,统治者自然不希望其他人知道这本书。
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也被誉为“兵学盛典”,但是这本书在历史上也经常被禁。因为统治者担心人民学会了其中的军事思想,对自己不利。但是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自己却要熟读此书。
还有一些书籍是与官方主流思想相悖,也是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
虽说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温和了许多,但是在禁书这个事情上,大伙儿都一样。
,这是一本典型以“人性本恶”为主题思想的书籍,很明显与儒家倡导的“人性本善”是对立的,由于他描绘的全是人性深处的“恶”,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负能量太多,所以也被禁止了。
我们印象中的《西游记》,据说因为尊佛贬道而触及了嘉靖皇帝信道的神经而被禁止,今天来看,《西游记》很多的内容不仅批评道教,连佛教也照批不误,更多的说法是因为
,因为异端邪说,上了明朝政府黑名单,所以和他有关的书自然也成为了禁书。
在当代多元化的社会,对各种观点都比较宽容,这些禁书大都重见天日。
我们发现,这些书籍被禁的理由,正是它价值所在,好比《
鬼谷子在书中所言:“捭阖者,天地之道。”“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是“谋之本,说之法。”
他把握住了天地人三材的运行发展规律,因此招招直指人心,教你把握时、势、局,洞察他人心理,占据搏弈制高点。
就像做游戏,你精通规则,便可步步抢先,有恃无恐。用句熟透的话讲,权谋之术也要符合“自然之道”,才是攻无不克的权谋,去创造历史,发挥自己独到的价值。
中国人无论说话办事、理家治国,一言一行都有这些禁书的影子。《鬼谷子》、《商君书》、《孙子兵法》都是从大千世界和人类社会抽象出来的智慧结晶。
说它们奇,因它们步步用奇,奇招迭出,招招见血,防不胜防;
说它们正,又因它崇尚“中正之道”,紧扣事物发展规律,可用来治国安邦,匡行大道:
说它秘,是由于两千年多来,它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时常靠它解决问题,而又对它知之甚少;
说它诡,则是由于它像极了一柄双刃神剑,用于正道可成一代宗师,光炳史册,用于邪道则为奸诈小人。
这便是这些禁书透露的思想,充满阴谋和大道,无所不出,无处不入,全看你拿来做什么!
对于我们而言,其中的阳谋——“大道”要学,阴谋也非常有必要学,明白了阴谋的原理,才能在竞争中,不着“阴谋”的道。
而且,这些禁书充满了辩证法,阴谋和阳谋可以转化,甚至本来就是一体!
不要忘了,谋略出自人,禁书的思想学完,无论阴谋阳谋,目的都是让自己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但是,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不可能每个人都是搞训诂学的专家学者,年代的久远,让我们无法直观理解个中奥义。
一者,很多禁书都是用晦涩的文言文写成,对于不是训诂专家的我们来说,要想搞懂,得下很大的气力;
再者,不少禁书倒是用了白话文,但是却用的是当时的民间俗语,还有方言,这对我们如何理解,也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最后,虽然是禁书,作者一开始让它面世的时候,还是想让它公开发行的,这种矛盾的心理,在书中我们如何捕捉到?
如果不能解决好上面的问题,我们对于这些禁书的真正闪光点是挖掘不到的,所以我们对禁书一直停留在好奇心上!
况且,那些今人解读禁书的书籍虽汗牛充栋,但鱼龙混杂,也有各种格调不高,几乎毫无益处的糟粕。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挑选其中的精品,去粗取精,不至于白白浪费时间与精力呢?
如今,你不必再有上述疑虑了,经过了数月精心准备,在梳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看鉴钻研大量古今中外知名禁书,最终选出等9本经典禁书,并推出一档全新的精品视频专辑——
推出这个系列并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期待打破大家“禁书=色情”的固有看法,了解到这些禁书创作背后的故事,内容梗概以及现实中的价值。
本次全新的看鉴禁书系列还有以下三大优点:
1)见解新颖,干货充实,我们另辟蹊径,选取原著要点,以全新视角解读中外禁书。
比如《甄嬛传》火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们认为作者文笔很好,然后编剧功夫过硬,实际上都不是!最大的功劳是雍正本人,他自己编撰的
康熙诸子勾心斗角,争夺储位这些套路化的宫斗故事,其实都是四爷自己亲口说出来的。
2)篇幅短小,可随时充电,每集持续时间最多为5分钟左右,在你等候公交,饭后睡前的碎片化时间里,随手点开一集即能迅速充电!
3)在知识性和方便性的基础上,我们的内容兼顾趣味性,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既可以达到休闲解压的目的,又可以加深记忆,成为与人交往的谈资。
相关资讯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古代小说简史》赵毓龙胡胜著辽宁人民出版社近年来,对文学史的研究逐渐成为学界一大热门议题。特别是针对体多性殊、时空跨度广、艺术边界相对模糊的中国古典小说而言,如何为之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