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略者的谎言,打着文明幌子做着肮脏交易
我们总说一段历史要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它才能是立体丰满的。一段历史故事就要听更多人口中的版本,因为不同身份的人会有不同的切入点,在口口相传中又会有无数个演变。去了解一段历史,在不同的本版中,我们要带着自己的思考,去辨别有用可靠的信息,在筛出来一份离真相蕞接近的版本。
在千百年的历史中,有着无数历史书籍,从《春秋》晦涩难懂的文言文,到如今分门别类的白话文历史书,总有一些书以意想不到的视角,带我们去看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
在华洋人的视角揭开中国口岸历史的神秘面纱,1832年~1914年,八十多年的时间是东西方平衡被打破的八十多年,也可以说是闭关锁国的大清被强硬打开按地上摩擦的屈辱史。从仅限于少量贸易往来的时间段,到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通商口岸。从鸦片侵蚀我国到那场变革的风暴。冲突还是误解,我看见的是中国人的觉醒。
以在华洋人的书信、日记、档案及主办的报刊等一手资料为出发点,重新去了解这段历史,你会发现故事的另一面,西方列强在华行为的逻辑是多么强盗,你也会看见一个洋人眼中的中国多么“秀色可餐”,更会了解到他们对中国的观察、看法和掉以轻心。
租界、通商口岸、海关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变迁,一桩桩一件件或大或小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的是西方列强对我们利益的瓜分,更让我们看见了中国人在打压之下的抗争,各个阶层的反抗有着强劲传染力,不屈服是烙在骨子里的尊严。
没有谁会在原地一直等你,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强盛,一旦开始固步自封那么也就开始了倒计时。大清帝国的骄傲伴随着不可一世悄悄落幕。鸦片侵蚀了国门,也腐烂了生活。如今禁毒有多严,曾经的伤就有多痛。不可以在一个地方摔倒两次。如今看着大.麻合法化的国家,不知道何时会重蹈我们曾经的覆辙,我相信天道好轮回。
动荡不安的年代,总有一些小丑想要轻描淡写那些真相。可是真相就是真相,永远不会被掩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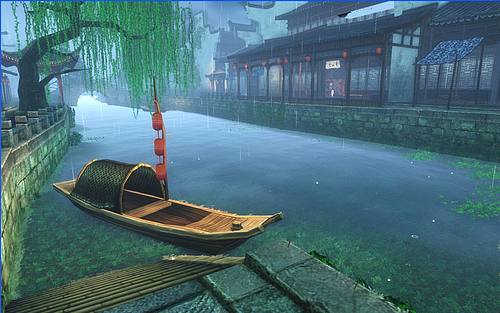
历史的良心
自从读了奥威尔的《1984》之后,对于反乌托邦小说就有一种偏爱和冲动。在我看来,反乌托邦小说描绘的是一种极端,它将我们的生活放大到一种极限状态,原本一些在现实中很隐晦很间接的行为,通过这种处理才能让人看清生活的这个世界有多么荒谬和可怕。通过小说来反思现实,它是在警醒我们,提高自己对于外界变化的敏感性。危险不是空穴来风,只是尚在我们的忍受限度之内;自由不是百分之百,只是递减的幅度让人难以察觉。如果我们稍有松懈麻痹,或者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反应不及,就极有可能一步步地丧失自由和权利。因此,才有这样一句话“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 《华氏451》里的蒙泰戈是一名消防队员,不过消防队员的职责不再是灭火救人而是放火焚书。当局不再允许人们拥有书籍,大部分人也想当然的认为书就像是我们现在的毒品,既然政府说它一无是处,那它就是十恶不赦,理应消灭。他们放弃书放弃地如此彻底,失去书籍没有让他们感到丝毫留恋。这其实就是一种极限化的夸张,反映的应该是布雷德伯利对于现代社会人类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迷失自己的追求,放弃阅读的忧虑。“书本的内容删得更短。精华本,文摘本,各种小报,所有的一切快得令人窒息,匆匆结尾。名著被删减成15分钟的电台话剧,接着又被删成两分钟的图书专栏,最后紧缩成10到12行的文字概要。文摘之文摘,文摘之文摘之文摘。政治?一栏话,两句话,一个标题!接着,半空中,全部消失不见了!出版商、开发商的巨手把人们的思想摆弄得团团转,飞速的离心机把一切不必要的、浪费时间的思想全都甩了出去!”这就是反乌托邦小说的魅力,如果把书变成一部电影、一场话剧或者一篇概要、几行文摘让你无动于衷,那么就干脆让书彻底消失,当原本正在逐渐丧失的东西突然灰飞烟灭,你还会感觉不到这种变化吗?小说加快了进度,夸大了程度,按下快进键带你提前看到故事的结局,以此来惊醒神经麻痹的读者去思考现实,提防危险。就像你没感觉到自己一天一天在变老,但是将三十年后的照片放在你眼前时,结果让人不敢正视。 书籍对我们有什么用?它是前人思想的结晶,人难免一死,但某些天才的头脑将他们脑中跳跃的电波转变成文字写在纸上,即使这头脑化为土灰,也依然让后人透过这些文字与他分享精神的果实。我喜欢俄罗斯诗人叶夫图申科写的《世界上的每个人都特别有意思》“每个人都有他的神秘世界,这世界有它最美好的时节,这世界也有最可怕的瞬息,可是这都不会为我们知悉••••••这就是这场残酷世界的规律,并非人死去,而是世界死去••••••人们一一离去,不可挽回,他们的神秘世界永不复归,就因为这一切的一去不返,每次都逼得我要放声呼喊。”而书就是留给我们窥探这失去世界的一把钥匙。加缪说:“穷人的命运就是无声无息地在历史中消失。”恐怕这个范围不仅是穷人,除了极少数杰出者之外,其他人都难逃此命。所以人们才愿意当作家,为这个世界留下点东西,也让后人知道曾经有这么一个人在地球上出现过。站在人类历史的角度,如果一个人死了就好像他从没来过这个世界,一代人消亡了就恢复到了他们出生之前,没有书作为载体将人类的智慧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文明又怎么会积累和发展。书就是巨人的肩膀,后来人借助它可以看得更多更远。一本传世名著被千万人阅读,那么当你也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无数人曾经或正在与你做同一件事情,你们也许会产生共鸣,也许看法大相径庭。但你们在读同一本书啊,透过书穿越时空将你与更大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你与读过这本书的人就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啊。你与也许数量多得你无法想象的人的头脑里都留下了这本书特有的指纹。是不是会有“天涯共此时”,“千里共婵娟”的感觉。书一方面教会我们知识,另一方面教给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不是每个作者看问题的角度都一样,即使对于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书里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你可以比较它们、思考它们,然后得出自己的看法,你就又有了自己的角度,自己的观点。 所有的专制政府共同点都是对思想的控制,统治者只希望人民知道他想让人民知道的东西,“愚民政策”让绝大多数人失去了解其他事物的途径,进而丧失思考的能力。当人们不知道别人的情况时,也就不清楚自己的位置。就好像你只读过一本书,你也就只知道这本书里的东西,凡是这本书里没写的,你都不会赞同。人们脑子里填充着着毫无意义的官话和浮夸的数据,人人却都以为自己知道的很多,人群当中没有异己,一百万个脑子只是将一个想法重复一百万遍,看不见差异,没有思想的交流,也就安于现状不会改变。专制统治者追求的就是这种效果,人民只听过他说的话,只接受指定的教育,那凡是他没说过的,自然不会被认可。 思考终究是人作为智慧生物的自然属性。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被愚弄,无论多么残酷的手段,一个社会总会有不甘于被控制,追求自由和独立的人。那么在书籍要完全消失的极端环境下,这类人就成为了传递文明的火种。作为书籍时代最后的孑遗,这些垂暮之年的老家伙隐藏在城市之外的荒野,为了安全将书印在自己的脑子里,溶于血液中,让自己成为书的载体,每个人就是一本书的扮演者。“他们根本不能确定,他们脑子里的东西是否可以给未来的每个黎明带去更加纯洁的晨光;他们什么都不敢肯定,只除了那些藏在他们宁静的眸子后面的书,那些书等待着,书页尚未分开,等待着多年后可能出现的顾客,有些人手指干净,另一些人手指肮脏。”他们是历史的良心,清楚地知道自己对于全人类的责任,无论采取什么方式必须将前人的思想传承下去。“基督之前,有一只叫做凤凰的该死的蠢鸟。每隔几百年,它就会筑起柴堆把自己烧死。它一定是人类的一位远亲。可是每次把自己烧死之后,它又会从灰烬中腾空而起,让自己得以重生。看来我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一次又一次,但是有一点凤凰是从来没有的。我们很清楚自己刚刚做过该死的蠢事。我们知道自己几千年来做过的全部蠢事,只要我们清楚这一点,而且总是把它放在可以看见的地方,那么总有一天,我们将不再堆砌那该死的火葬柴堆,不再纵身跳到火堆里去。每一代我们都会多选几个人来记住这件事。”不过书也不是包治百病的,历史最大的教训就是从来没有人吸取历史的教训。从来可能过于绝对,但正是因为忘记过去的苦痛,所以才会照样再犯前人犯过的错误。
羞耻往事的真相
这本很薄,看上去很轻巧的书里记录的却是一件沉重可怖的往事。开篇第一句便是:
当时还不满12岁的埃尔诺并不明白父母间发生了什么。但这一场景在她此后的人生中反复侵入大脑,令她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中满是令人羞耻之事。但“羞耻”的感受根源在哪里,又是如何产生的,她并未认真思考过。于是事情发生的四十年后,埃尔诺决定动笔写下这件事。找出令她产生羞耻的事物和根源。
在父母都已去世,无从询问当事人的当下。最直接的线索便是当时身处现场的自己。埃尔诺找到了那年的两张照片、一些明信片、一个工具包和一张乐谱,又去图书馆翻阅了事发当天的报纸。她发现:
从时代背景、城市的历史,到家族历史、个人历史。无形的线将一切串联,编织埃尔诺故乡人们的普遍形态。大家彼此熟悉也彼此观察,好方便聚在一起说闲话。人们大多使用方言、在工厂工作,有自己的日常习惯动作。比如:女人会四肢着地擦地板、男人会在耳朵上夹一支烟。
如果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想必埃尔诺对那件往事不会如此耿耿于怀。因为此地的人们都认为家人间的礼貌是虚伪,而粗暴和喊叫反而被视为正常。令她意识到自己生活在无尽“羞耻”中的,是天主教私立学校的教育。
这里纪律严明,教师多是修女,除了神父和园丁外没有男性。在这里上学的也基本是拥有资产且重视教育的家庭中出身的女孩。
这就帮助埃尔诺在家也能按学校系统中的规则生活。并且,母亲还灵活改变了其中她认为刻板,不利于个人发展的部分。
比如:学校不允许学生阅读宗教经典之外的书籍,但母亲却买了一堆小说和杂志自己读再转给女儿;她认为宗教只能作为辅助,不能取代具体的算数与拼写教育;她绝不愿女儿成为修女。
这里尽管只有短短两三页的描写,但我已经深深感受到了埃尔诺母亲独特的个人意志与性格。书里写
埃尔诺的父亲则与之相反,他不信教也没什么提高自己地位的欲望。教育孩子的事基本交给母亲。他最在乎的是孩子是否合群。
令埃尔诺耿耿于怀的事件简直就像两种价值观的一次激烈对抗。其实我明白,把这件残酷的事抽象表述并不合适。她的父母当时必然也是因为某种具体的争执而产生的冲突。
这件事的影响如此深重,埃尔诺开始意识到自己生活的家庭和学校完全是两个世界。她甚至觉得自己已经
这里的“优秀”、“完美”可以打上引号。对于那个十二岁的女孩来说也许的确如此,但对四十年后的埃尔诺来说,她明白正是这种认知造成了“羞耻”。
私立学校象征的世界文明、洁净、秩序井然;而家庭象征的世界则暴力、肮脏、混乱无序。埃尔诺在书的最后说:
关于阶级、资本如何令贫穷的人们被迫从事被视为不光彩,甚至是带有道德污点的工作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看看《脏活》这本书。之前的视频中也分享过,这里就不赘述了。
本书中埃尔诺拒绝心理分析式的书写。她认为“情感创伤”、“家庭权力争夺”之类的术语过于抽象,无法更本质地揭示事件与情感背后的真相。她要把构建了这些的语言、文化和固有价值观统统揭露,把
这便是埃尔诺写作的方式,也是她致力于达成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