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佛山人”的骄傲
近代中国处于晚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之下,内忧外患的社会现状,黑暗压抑,乱象频生。有识之士,在沉闷中彷徨,寻求救国治愚之道。于是谴责小说流派悄然兴起,发展成为潮流。清末四大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是其中的代表作。这类小说“揭发伏藏,显其弊恶”,对于启迪民智、改革社会产生了积极作用,形成了强大而深远的影响力。各位谴责小说家们也几乎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化名人。
(1866—1910),名沃尧、宝震,字小允,号天南遁叟,又号我佛山人,广东佛山人。本期佛山历史文人故事会,让我们一起走近吴趼人,探寻一个清末的佛镇少年如何在时代的大潮中奋力遨游,成长为一代沪上小说名家的故事。
清同治五年四月十六日(1866年5月29日),吴趼人降生于北京宣武门贾家胡同其祖父吴尚志的“分宜故第”,父亲升福。祖父尚志,为吴荣光次子。吴荣光,清嘉庆四年(1799)进士,官至湖南巡抚、湖广总督,是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且精词章、金石、训诂之学,善书法,又是著名的学者。
吴趼人祖上家世显赫。在岭南老家佛山,大树堂吴氏乃名门望族、官宦大家。尤其是曾祖父吴荣光以其学术成就和封疆大吏的资历与威望,将家族地位推向高峰。但是随着吴荣光的去世,家族盛极而衰,逐渐没落。
吴趼人出生不久,祖父尚志去世。清同治六年(1867),失去祖上庇佑的父亲吴升福携着妻子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吴趼人扶柩还乡,千里归根,回到已经没落的佛山大树堂。后来不久,吴升福就为生计离开妻儿,到浙江去做小吏了。
吴趼人的童年与少年时代就在佛山度过,直到17岁时父亲又在浙江任上去世,他为奔父丧离开佛山。期间没有父亲的保护,吴趼人与母亲、妹妹相依为命,不断受到族中“豪家”的欺压,备尝艰辛。
1884年,18岁的吴趼人,在经历父丧之痛,生活无着,意欲挣脱没落大家族恶劣桎梏的境遇下,来到新思想新文化发展最快的上海闯荡。吴趼人初到上海,先投靠同乡江裕昌茶庄,后来进入江南制造总局做抄写和绘图员。虽然月入微薄,但是上海开放先进的社会环境与家乡古镇迥然不同,令吴趼人大开眼界。其中与各方人士的交流周旋,让他受到新思想的冲击,渐渐思考更为丰富而有价值的人生出路。据说吴趼人有一次从书坊购得半部《归有光文集》看的爱不释手,从而迸发了对文学的热爱和写作的热忱,渐渐地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1897年吴趼人离开了服务十几年的江南制造局,受聘为一些小报主笔,先后主持了《消闲报》《采风报》《寓言报》等。经过五六年的报人生涯,面对国家社会的种种巨变,吴趼人又陷入了新一轮的人生价值的自我拷问与求索中。
1903年经历一番痛苦的思索之后,吴趼人决定全力投入小说创作,呼应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杂志所鼓吹的“小说救国论”。于是吴趼人先后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九命奇冤》等小说书稿寄往《新小说》上发表。吴趼人从此笔耕不辍,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写情小说、笑话小说多头并进,一发不可收拾,直至1910年因病去世,作品总字数超过300万。
吴趼人的小说创作纵横捭阖,题材广泛,嬉笑怒骂,寓庄于谐,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揭露了社会黑暗、政治腐败,获得强烈的社会反响。通过在小说界的辛勤耕耘,吴趼人文名日盛,成为著名的职业小说家,也在践行自己“借小说之趣味之感情,为道德之一助”的小说理论中,实现自己所追求的人生价值,破茧成蝶,在文字是世界里自由驰骋。
三、蜚声海内,我佛山人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吴趼人的笔名很多,而以“我佛山人”最为人们所熟知。 “其先卜居佛山,凡所撰述,因署端曰: 自士夫以及贾竖,有不能名君字君者,称我佛山人,未尝不颔之若稔识。 ”可见“我佛山人”在当时的闻名程度。
吴趼人的作品很多,而以署名“我佛山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为出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吴趼人第一部著名的代表作,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本书通过主人公“九死一生”以第一人称叙述了自己从奔父丧开始,至经商失败止,所耳闻目睹的近200个小故事,勾画出1884年到1904年前后20年间,社会上的种种怪现状,揭露了晚清官场的腐败,以及社会道德风尚的堕落。
这部小说是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与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齐名,但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比《官场现形记》更为广阔,除官场外,还涉及商场、洋场、科场,兼及医卜星相,三教九流。胡适曾说“故鄙意以为吾国第一流小说,古惟《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四书,今人惟李伯元、吴趼人两家,其他皆第二流以下耳。”《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深入民心,蜚声海内,奠定了吴趼人在中国近代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初发表于《新小说》书影
纵观吴趼人的一生,他从传统没落大家族的桎梏之中走出,在晚清新旧交替、中西碰撞的浪潮中,经过不断地反省、探寻、突破,努力做着有补于社会道德,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尝试,最终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奔驰不息,至死方休。吴趼人共创作了中长篇小说17部,短篇小说13篇,笔记6种,笑话3种,寓言1种,文集2种,戏曲2种。这些作品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并进行了新的艺术探索,对后世影响深远。
任百强著《吴趼人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
卢叔度主编《我佛山人文集》,花城出版社,1988年
索书号:K825.6=5/R425/2
馆藏地:佛山市图书馆五楼地方文献阅览区
索书号:I242.4/W805/-6
馆藏地:佛山市图书馆三楼图书借阅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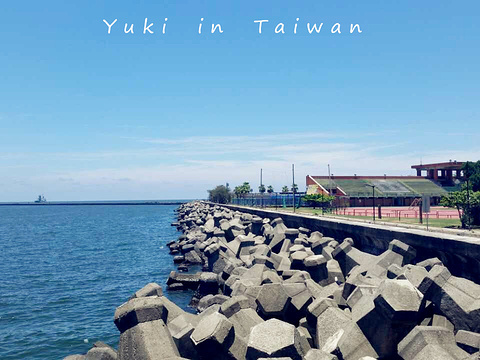
再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什么专制社会中的官吏这么荒唐?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创作于1903年,同年于《新小说》上连载,后1909年完成,共一百零八回。与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一起并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对晚清官吏的腐败龌龊、官僚的卑劣无耻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小说中九死一生说:
要做官就要搁过良心,要学会卑污苟贱,就是“为官”和非道德规范之间的内在联系呀。“千里做官只为财”竟成了一条不言自明的逻辑。小说以大量官场的种种丑闻向我们展示了这种难以理解却又司空见惯的现象。
小说第五十九回,一位京官因听信谣传紫禁城埋了炸药,竟将二十余条无辜生命赴诸市曹。六十一回,因为一位差吏走眼,误将树影看成人影,以为有盗贼,竟调兵遣将,兴师动众,足足闹了几天。
九十五回,旗人观察苟才在安徽银元局总办任上被参,他又以六十万两银子让此事偃旗息鼓,原来这下来巡视的九省钦差自己就是个“色厉内荏之流,外面虽是雷厉风行,装模作样,其实说到他的内情,只要有钱送给他,便万事全休了”。由起初一个“吃尽当光”的穷观察到后米“宦囊丰满,不在乎差使”的地步,苟才用钱填平了他仕宦途中的所有坎坷。
这些官吏们,他们判案可以任情武断、胡作非为;带兵打仗,他们可以一味腐败、营私舞弊。用金钱去逢迎巴结上司,用银两去铺砌一级一级向上爬的台阶。形成一种“大鱼吃小鱼,小鱼吞虾米”的混乱局面,真的用金银财宝“拼成功一个贿赂公行的世界了”。总之,在小说中“官”字一词,已不再具有它的尊严,什么污七八糟的有钱人都可以由捐纳一途大过官瘾。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我们展现出晚清官吏的黑暗。那些所谓的理想早已被抛弃,就连儒家文化自己说的“仁政”都沦为笑柄。只有赤裸裸的金钱至上,只有“男盗女娼”,腐败堕落、荒唐可笑充斥着整个官场。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那个时代,官吏们都是如此庸俗不堪,是如此的荒唐,正因为官吏们——这个社会的管理阶层都是这样。他们挥舞着权力的大棒对民众是肆意妄为、为非作歹、高高在上,所以使得整个社会表现出极大的荒诞和荒唐,民众也是饱受剥削、压迫,整个社会黑暗无比。
晚清官吏表现出来的种种现象和行为直接揭示出社会走向末日时期的管理阶层状态。官僚制度弊端百出,根本原因在于专制。权力高度垄断,垄断于君主,君主凌驾于一切法律和制度之上,不受任何限制、制约、约束和监督。
权大于法,实行人治。君主一个人说了算,说的话是圣谕,要聆听,下达的书面指令是圣旨,没有人敢不遵守。
君主通过自上而下层层任命官吏的方式来完成权力的确定和行使,导致官吏的权力来源于君主和上级,而不是人民,人民也没有权力来监督官吏,能够监督官吏的只有上级和君主。而能够任命官吏的也只有上级和君主。
所以官吏们根本不怕民众,根本不需要想到民众,民众只需要按照官吏的意思照做、照办,遵守服从就行了。要做就要做顺民,服从为主。
所以整个社会表现出了极大的荒诞,因为官吏的指令有时候是错的,哪怕是错的很离谱,民众都要去服从和顺从。而官吏们由于缺乏监督,所以他们可以随心所欲,想怎么弄就怎么弄,表现出了极大的随意性、自私性和逐利性。
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我佛山人,上海的小说名家
近代中国处于晚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之下,内忧外患的社会现状,黑暗压抑,乱象频生。有识之士,在沉闷中彷徨,寻求救国治愚之道。于是谴责小说流派悄然兴起,发展成为潮流。清末四大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是其中的代表作。这类小说“揭发伏藏,显其弊恶”,对于启迪民智、改革社会产生了积极作用,形成了强大而深远的影响力。各位谴责小说家们也几乎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化名人。
(1866—1910),名沃尧、宝震,字小允,号天南遁叟,又号我佛山人,广东佛山人。让我们一起走近吴趼人,探寻一个清末的佛镇少年如何在时代的大潮中奋力遨游,成长为一代沪上小说名家的故事。
清同治五年四月十六日(1866年5月29日),吴趼人降生于北京宣武门贾家胡同其祖父吴尚志的“分宜故第”,父亲升福。祖父尚志,为吴荣光次子。吴荣光,清嘉庆四年(1799)进士,官至湖南巡抚、湖广总督,是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且精词章、金石、训诂之学,善书法,又是著名的学者。
吴趼人祖上家世显赫。在岭南老家佛山,大树堂吴氏乃名门望族、官宦大家。尤其是曾祖父吴荣光以其学术成就和封疆大吏的资历与威望,将家族地位推向高峰。但是随着吴荣光的去世,家族盛极而衰,逐渐没落。
吴趼人出生不久,祖父尚志去世。清同治六年(1867),失去祖上庇佑的父亲吴升福携着妻子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吴趼人扶柩还乡,千里归根,回到已经没落的佛山大树堂。后来不久,吴升福就为生计离开妻儿,到浙江去做小吏了。
吴趼人的童年与少年时代就在佛山度过,直到17岁时父亲又在浙江任上去世,他为奔父丧离开佛山。期间没有父亲的保护,吴趼人与母亲、妹妹相依为命,不断受到族中“豪家”的欺压,备尝艰辛。
1884年,18岁的吴趼人,在经历父丧之痛,生活无着,意欲挣脱没落大家族恶劣桎梏的境遇下,来到新思想新文化发展最快的上海闯荡。吴趼人初到上海,先投靠同乡江裕昌茶庄,后来进入江南制造总局做抄写和绘图员。虽然月入微薄,但是上海开放先进的社会环境与家乡古镇迥然不同,令吴趼人大开眼界。其中与各方人士的交流周旋,让他受到新思想的冲击,渐渐思考更为丰富而有价值的人生出路。据说吴趼人有一次从书坊购得半部《归有光文集》看的爱不释手,从而迸发了对文学的热爱和写作的热忱,渐渐地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1897年吴趼人离开了服务十几年的江南制造局,受聘为一些小报主笔,先后主持了《消闲报》《采风报》《寓言报》等。经过五六年的报人生涯,面对国家社会的种种巨变,吴趼人又陷入了新一轮的人生价值的自我拷问与求索中。
1903年经历一番痛苦的思索之后,吴趼人决定全力投入小说创作,呼应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杂志所鼓吹的“小说救国论”。于是吴趼人先后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九命奇冤》等小说书稿寄往《新小说》上发表。吴趼人从此笔耕不辍,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写情小说、笑话小说多头并进,一发不可收拾,直至1910年因病去世,作品总字数超过300万。
吴趼人的小说创作纵横捭阖,题材广泛,嬉笑怒骂,寓庄于谐,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揭露了社会黑暗、政治腐败,获得强烈的社会反响。通过在小说界的辛勤耕耘,吴趼人文名日盛,成为著名的职业小说家,也在践行自己“借小说之趣味之感情,为道德之一助”的小说理论中,实现自己所追求的人生价值,破茧成蝶,在文字是世界里自由驰骋。
三、蜚声海内,我佛山人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吴趼人的笔名很多,而以“我佛山人”最为人们所熟知。 “其先卜居佛山,凡所撰述,因署端曰: 自士夫以及贾竖,有不能名君字君者,称我佛山人,未尝不颔之若稔识。 ”可见“我佛山人”在当时的闻名程度。
吴趼人的作品很多,而以署名“我佛山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为出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吴趼人第一部著名的代表作,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本书通过主人公“九死一生”以第一人称叙述了自己从奔父丧开始,至经商失败止,所耳闻目睹的近200个小故事,勾画出1884年到1904年前后20年间,社会上的种种怪现状,揭露了晚清官场的腐败,以及社会道德风尚的堕落。
这部小说是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与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齐名,但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比《官场现形记》更为广阔,除官场外,还涉及商场、洋场、科场,兼及医卜星相,三教九流。胡适曾说“故鄙意以为吾国第一流小说,古惟《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四书,今人惟李伯元、吴趼人两家,其他皆第二流以下耳。”《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深入民心,蜚声海内,奠定了吴趼人在中国近代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初发表于《新小说》书影
纵观吴趼人的一生,他从传统没落大家族的桎梏之中走出,在晚清新旧交替、中西碰撞的浪潮中,经过不断地反省、探寻、突破,努力做着有补于社会道德,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尝试,最终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奔驰不息,至死方休。吴趼人共创作了中长篇小说17部,短篇小说13篇,笔记6种,笑话3种,寓言1种,文集2种,戏曲2种。这些作品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并进行了新的艺术探索,对后世影响深远。
任百强著《吴趼人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
卢叔度主编《我佛山人文集》,花城出版社,1988年
索书号:K825.6=5/R425/2
馆藏地:佛山市图书馆“知书达里”预借库
索书号:I242.4/W805/-6

